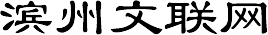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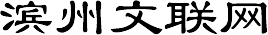
伏生故里系魏桥镇冢子村考略
王大生
伏生是彪炳史册的史学翘楚,是两千多年前今文《尚书》最早并且是唯一的收藏者、整理者和传播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位巨人,自西汉以来一直受到膜拜和尊崇,影响深远,贡献至伟。但是关于他的故里、墓葬等问题,一直存在谜团和争议。隋唐时期历史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经非伏生作,似与邹平无涉。然当汉文之世传《尚书》者,惟伏生一人尔。”清成瓘说:“汉初《尚书》惟伏生今文一本,出最先,传之者亦最众。”伏生生前,秦时被征诏为博士,汉文帝时应诏传太常掌故晁错于《尚书》,从此名传天下,彪炳青史;去世后,唐贞观21年被太宗下诏配享孔子庙庭,尊为圣人,与孔子一起享受百姓万民祭祀,到了宋真宗咸平四年又被朝廷追封乘氏伯,其后世子孙也世袭五经博士之荣光。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尤其是秦汉文化,甚或上古历史,是绕不开伏生的,那么伏生的故里究竟是在哪里呢?《史记·儒林列传》和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均说“伏生者,济南人也”,但都没有具体说伏生是济南哪里人?此时的“济南郡”属地广阔,隶10余县,这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遐想的空间,成了千古之谜。笔者遍查并综合案头文献和媒体网络报道、信息,甚或是轶闻杂谈后认为:说济南者,是举伏生汉属济南郡人说事;说章丘者,是因伏生家乡汉属济南郡而郡治所在东平陵,即今山东章丘境为据;说聊城阳谷宓城(伏城)者,是因伏生躲避战乱流寓之地所在。说滨州邹平者最为凸显,一是因今邹平韩店镇有伏生祠与伏氏后人居住,二是因今邹平魏桥镇有汉代伏生墓。在邹平韩店镇说中,又有苏家村说、东颜李村说、旧口村说等,皆因其村与伏生祠相邻之故。济南、章丘、宓城并以上诸说,缺少实证,与历史不符,不能成立。唯今邹平魏桥镇冢子村为伏生故里说,依汉代伏生之墓和冢子村与诸多史料为依据,经得起考证与推敲。由于伏生故里争议由来已久,也由于伏生在滨州传统文化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寻找论证和准确地定位伏生故里也成了当今滨州文史爱好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笔者以为,厘清或了解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对拨开历史疑云,确定今邹平市区域内的魏桥镇冢子村是汉代伏生的“栖息之域”,是其真正的故里,有着积极意义。

王维《伏生授经图》
一、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与伏生故里
自汉、唐、宋以来有据可查的史料,基本均认定魏桥镇冢子村的伏生墓为汉代墓葬,是秦博士伏生之墓,又名汉徵君伏生墓、伏徵君墓、伏夫子墓、寄驾冢,位于今魏桥镇冢子村西南。民国《邹平县志·方域沿革图》有图一汉魏晋;图二宋魏齐隋;图三唐宋;图四金元明;图五今治(清)。图一“汉邹平县、梁邹县、东邹县、魏晋邹平县、梁邹县图考”中,在古济水旁汉梁邹县治旧口(今韩店镇)地有祠庙标识,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伏生祠的位置,但标注文字为“伏生故里(疑故里为“祠”之误写,见下图四图五之标注)。”同时该《方域沿革图》还在漯水旁标明了今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位置与“伏生墓”字样,县治注明是“东朝阳”。图后附注:“梁邹城在今治东北二十里旧口。”在该图四、图五同样位置标识有祠庙标志,图一中注明的“伏生故里”改称了“伏生祠”。图五将图一中的“伏生墓”也改称“寄驾冢”。古县治所在与《方域沿革图》吻合。这昭示着今韩店镇伏生祠和今魏桥镇伏生墓,在伏生死后最晚魏晋以前就成为了一个世可公认的地理坐标。在汉梁邹县治所有祠庙、在汉邹平故里家乡有坟冢,明确的地标物证,证明了汉伏生祠墓的真实所在。
在今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遗址,现有“徵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碑石两通。1980年,被邹平县革命委员会公布为邹平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网络魏桥镇政府介绍:“古迹有秦博士伏生墓。”又,“伏生,战国末年齐国人…伏生去世后,诏立汉征君伏生墓,位于今魏桥镇冢子村西。伏生墓基宽19米,长30米,高6米,墓旁有亭堂书院,唐槐古松,十分壮观,墓西有大片梧桐树林。1950年以前,墓地一直有人守护。”明明白白告知后人,伏生是这里人、死后葬于家乡故里。《邹平地名故事》魏桥伏生墓说:“这个冢子其实是一个汉代的古墓,是秦汉时期博士伏生的墓葬,后讹称作寄驾冢,人们几乎忘了它是伏生墓了。”清成瓘《伏夫子墓考》载:“古言征君墓者,唯云在朝阳城东而已。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出始举其里数之。记云:伏生墓在朝阳城东五里,是征君墓在宋太平兴国时尚可如此确指,必当年祠宇或汉碑或唐人表彰古迹之碑犹有存者,不然乐氏何据而如此凿凿言之邪?”宋太平兴国时是公元976年—984年,也就是说,这证明了宋代早期所确指的伏生墓位置就是今魏桥冢子村所在。清康熙新修《齐东县志·卷二》载:“寄驾冢,在城西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八尺,周围七十八步。”中国历代王朝对墓葬制度有严格的规范,汉代传承秦国的二十等爵制。伏生去世后,享受侯爵之标准,魏桥镇之伏生墓契合汉代侯爵墓葬之规定。民国《齐东县志·卷六艺文志》载齐东县知事蓝鸿䎝说:“《山东通志》则据《邹平县志》谓伏生墓实在邹平。然考《水经》云:漯水,又东北经崔氏城北,又东南经东朝阳县故城南,又东经汉伏征君墓南,又东经邹平县古城北……。”又民国《齐东县志·卷二地理志》载:“伏征君墓,在今城西偏北三十里寄驾冢庄西。查邹平亦有伏生墓,《邹平县志》谓伏生墓在城东北十八里,与本县伏生墓相距约八十里。《续山东考古录》认为齐东寄驾冢是在邹平者,疑冢也。”又载:“况邹平城东北之伏生墓距寄驾冢八十里,无论邹齐分界与否,按其位置,与《水经》、《寰宇记》所谓伏生墓者,曾不相涉,认为疑冢洵非巫也。”其论断就是邹平韩店之“伏生墓”是疑冢,而魏桥镇之伏生墓方为真墓。从宋《太平寰宇记》到清末的诸多文献考证,字字句句,论定了汉伏生墓之所在,同时也为伏生故里在今魏桥镇冢子村夯实了坐标。又如,清齐东县知县宫耀月在《重修伏征君墓碑》中说:“窃尝遐稽往迹,博采传言,以为邹平县有伏生塚,考之各书均有未合,或曰此疑塚也。将安往而识其真耶?丙申春,服官来齐,因公赴乡,路经寄驾塚偶憩焉。徘徊展望,见一塚上有庙,问之乡人,一人拱立而言曰:泰山行宫。问其塚,曰寄驾塚。何谓寄驾?曰俗传唐王征东,寄驾于此,故以寄驾名。自寄驾之名出,人遂不复问其塚之所由来。问何谓也,曰此先儒汉征君伏生墓也。余闻之,余心焉异之曰:伏生墓乃在斯乎?及返而考诸《水经注》、《广舆记》、《环宇记》、《大清一统志》诸书,历历稽之不爽焉。”宫耀月的实地考察从诸古籍中得到了证实,确认了这里就是伏生真墓。又,清成瓘撰《伏夫子墓考》在总结了前人文献后,以五个方面证实了今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之实。他说:“言征君墓者,证诸元初人之书又确乎其有据也。壬戌八月,自魏王城循千秋岭河岸东行,果遇一大邱,曰寄驾冢。南望千秋岭不盈半里,与《水经》漯水经其墓南语合,可信为征君墓者一也。西望东朝阳不盈不绌,恰符五里,与《寰宇记》、《齐乘》语又合,可信为征君墓者二也。《水经》漯水又东经邹平县故城北,由冢东望汉邹平故城之在孙镇者,方向及川渠并合,可信为征君墓者三也。囗北广南狭,如古马鬛封之制,附冢有方台,广数亩,在冢东南台中,时有古瓦,又如古享堂之制。征君在汉时尊为先师,故其墓制享堂制亦似仿曲阜之制而为之,可信为征君墓者四也。冢西南五里有甜水庄,古云皇辛庄。详其文字,当是皇亲庄之讹。伏氏在汉时,世受侯爵,为显官,男尚公主,女为贵人,为皇后,虽久徙居东武,而祖墓在此,岂无居而守墓者?若是,则皇亲庄之流传果有所自矣,可信为征君墓者五也。”又,清柳文洙撰写的《重修伏征君墓碑》中,指出了所建伏生祠与墓不在一起,以及后人不考沿革等,对今人正确理解伏生墓、祠及伏生故里所在颇有意义。如曰“齐东县西南三十里有朝阳故城,俗名魏王城,东五里汉伏生墓在焉。地於赵宋属邹平,宋咸平时封伏生为乘氏伯,建祠于今邹平县治东北十八里,距墓尚远。至元析邹平地置齐东,祠墓遂分属两县。后人不考沿革,既误求伏生墓於宋以后之邹平。又狃於祠在是墓必在是,辗转伪口均谓墓在邹平,而齐东之邱垄见于《水经注》、《寰宇记》诸书,转无人核其实而为之表彰者。”笔者认为,宋封乘氏伯后建祠虽说是一种推理,然却说明了在距伏生墓数十公里之外的旧口地建祠,墓祠分设,是官方有意为之。又,清廪膳生、民国山东省临时省议会议员李炳炎先生在其《伏生墓序》中,专门论述了伏生墓所在与隶属,寥寥数语,把人们关心的伏生墓说的明明白白:“漯水东南,经东朝阳故城南,又东经汉征君伏生墓,此《水经》之伏生墓也。临济县东四十里有东朝阳城,伏生墓在城东五里,此《寰宇记》之伏生墓也。漯水有伏征君墓,此宋之《博物志》之伏生墓也。以上伏生墓之故址,皆在齐东县之寄驾塚。《邹平县志》伏生墓,在今邹平城之东北一十八里,系旧口镇地…则邹平之伏生墓似可谓证据详明矣。然考两墓之距离,约六十余里,在西北者齐东之伏生墓,在东南者邹平之伏生墓…《齐东县志》无伏生墓而有寄驾塚。”又曰:“一伏生墓也…何许子之不惮烦也!盖以先贤之墓,辨之不明,志之不详,令后人一误再误,而于崇拜公理,未能恝然也。”(摘自《东野轶闻校注》)。可见先生关心伏生墓争议的原因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为了不让后人一误再误。
祠与墓不同,按中华文化惯例,凡名人建功立业之地,均可为其立祠。但真实墓葬,一般都会归葬家乡。倘若不是特殊原因,人死后葬在故里家乡的土地上,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的重要体现,这种“叶落归根”的思想从上古至今,根深蒂固,亘古难变,融化到了国人魂魄之中,想必两千多年前的伏生也不会例外。伏生去世时,汉已平定天下,四海升平,步入盛世,且他本人备受朝廷尊崇,名震天下,生于斯,葬于斯,所以墓确实应该在他的家乡故里。

话剧《伏生》剧照。
二、邹平、齐东两县分与合与伏生故里
伏生故里纷乱之争,尤其是魏桥镇与韩店镇之说与邹平、齐东两县分与合有关。故厘清邹平、齐东两县之分与合的大体过程,有利于明确伏生墓、祠与故里的关系。
明代之前,魏桥镇冢子村原本属于邹平县境,康熙新修《齐东县志》曰:“元太宗七年(笔者注:民国《邹平县志》、民国《齐东县志》皆说元宪宗二年。疑误),析邹平、章丘县地,以邹平齐东镇立齐东县,属河间路。”之后,“明洪武十二年,割邹平会仙、齐东二乡…以增之。”伏生故里冢子村与村西南伏生墓原本就隶属邹平会仙乡,所以自明洪武十二年会仙乡割入齐东县以后,今魏桥镇伏生墓脱离邹平隶属齐东县境。原属邹平在今韩店镇地的伏生祠和今魏桥镇地的伏生墓就分属了邹平、齐东两县境,相隔六十里,自此邹平就只有伏生祠再无伏生墓了。如成瓘在《伏夫子墓考》中说:“地为会仙乡,按此则是邹平故地,明时割入齐东县境者。”直到1956年3月,高青县与齐东县合并为齐东县,县治田镇镇,隶惠民专署。1958年11月,又将齐东县析入博兴县、邹平县,皆属淄博专署。至此,伏生故里冢子村和伏生墓又重新回到邹平县境,此时伏生故里冢子村离开邹平县域已长达579年。1958年,具有723年历史的齐东县建置,也在经历了元、明、清、民国与新中国成立九年后消失。
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邹平县尹曹叔明重修今韩店镇伏生祠时,请当时朝廷名臣章丘人张起岩为其撰写《修祠记》,其中曰“济南邹平县治东北十余里,号伏生乡,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据考,就是张起岩一句“伏生之墓在焉”和“即墓所有祠”,改变了人们对今韩店镇只有祠没有墓的认知,成了伏生故里韩店说依据之源,引起了700年的伏生故里聚讼。后世不乏对张起岩“伏生之墓在焉”和“即墓建祠”说提出质疑者。民国《邹平县志·卷九古迹考二》所载“城东北十八里伏子祠…谓有墓者,始于元张起岩撰《修祠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又如清成启洸在《伏征君疑冢辩》中说:“元至正时,碑云旁有道士墓,县尉王君命徙之。元时伏子祠实为道流栖息之所…祠旁一墓,自元迄今逾四百年。”提出了伏生祠旁有“道士墓”之说,不是说祠旁有伏生墓,而是有一座道士墓,对韩店伏生墓与故里说提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质疑!若此说无误,必是有道教人员已经长期在此栖息生存若干年,死后就葬于伏生祠旁。张起岩提出“即墓所有祠”、成启洸提出了“碑云旁有道士墓”,两位前贤定不会是无中生有。祠旁有道士墓言之凿凿,不然就不会有“县尉王君命徙之”之说。既然二位说的都是元代,那张起岩所说的“墓”会不会是成启洸说的“墓”呢?如确有道士在此长期居住,又有道士墓在,那“元时伏子祠实为道流栖息之所”也不会是假的。可见此时,伏生祠之地还没有伏姓后人在此定居奉祭祀护卫之责,也说明官府对伏生祠疏于敬重管理。至于元末伏氏后裔伏步迁徙旧口地时,是否还有道士栖息于此就不得而知了。
邹平人或齐东人都知道伏生墓与祠两地相隔,然自分为邹、齐两县,尤其自从《邹平县志》、《山东通志》承续了张起岩“即墓建祠”说之后,视今韩店镇为伏生故里说日益凸显,然却忽略了今魏桥镇冢子村当年还有伏生后人和其汉代祖墓的存在。直至清代,虽有众多名士、文人和史据呼唤伏生故里真相,但限于邹平、齐东分治,朝廷忽略,时局动荡,一直没有公众认可的定论。

伏生祠赑屃
三、魏桥镇冢子村伏氏家族与伏生故里
1992年版《邹平县志·卷一建置》载:“冢子,春秋战国时建村,有伏姓居住,伏胜死后葬此。汉修伏征君墓周围形成三个聚落,即袁家冢、李家冢、王家冢。唐朝后,相传太宗东征寄驾于此,因名为寄驾冢。1982年定名为冢子村。”相传,直至清同治年间,这里曾是伏生及后人世代生活的地方,然不知何故今已无伏氏后人在此居住,但村内历史上曾有的“伏家巷”和现“伏生墓”遗址,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据考证,清同治时,还有伏生后人在冢子村生活。民国八年,李炳炎先生撰《汉征君石》说:“寄家冢村外,有伏生墓及祭田四十亩。同治前,墓碑犹存,后为伏氏后裔割鬻及邻人侵占,祭田几尽。闻上宪有查追之耗,占田者竟碎其碑,埋污泥中。光绪初,邑人孟继和负笈省垣,撰修墓公启…。”其又撰文《伏氏族谱》说:寄家冢村,旧有伏氏数家。以贫甚不能读书,故其族皆椎鲁。同治间,上宪访伏氏后裔及其墓田。伏氏子某持《家乘》,商于魏家桥魏某。云:闻若墓田已迷失,倘献《家承》,上宪追问,恐干重究。不如焚之,以绝后患。伏氏子从之。”(见《东野轶闻校注》)。李炳炎先生生于清同治七年,即公元1868年,其故里李码村与冢子村相距不过5公里左右,而炳炎先生为文化名士,见闻极广,本乡里间事情更为熟知,其年少时冢子村还有伏姓居住,应是亲闻、亲历,故其说可信度极高。可以看出冢子村伏生后人家境衰落,因贫不能读书而“椎鲁”,竟然做出了焚烧《伏氏族谱》之不尊不敬不贤不孝的荒唐事。也看出他们家族长久以来,善良卑微受人欺,以及祭田被邻人侵占,甚至先祖伏生坟上建碧霞元君祠、墓碑被人砸碎埋于污泥中,都没有见到任何伏氏家族及后人反抗或表示不满或提出异议的记述,揭示了伏生后人较长时期的生活之艰难,村中地位之卑下,甚至说活的有些“窝囊”。虽然如此,但也可以证明,冢子村伏生后人自汉至清末两千余年都以冢子村为故里,在这里繁衍生息。从史料中查到的伏生后裔清末同治年间割鬻祭田、焚烧伏氏族谱等活动轨迹和村中旧有的伏家巷,以及现存的汉伏生墓遗址分析,都说明此地当属伏生故里无疑。
四、魏桥镇冢子村伏生祠与伏生故里
绝大多数历史典籍载明,伏生墓与祠是分设的,伏生墓在邹平西北,伏生祠在墓之东南,相距30公里。有学者认为,位于伏生故里今魏桥镇冢子村西南的伏生墓,从汉至清末两千多年,本来只有墓没有祠,但不知何时却在偌大神圣的伏生墓区没建祭享祠,却在墓上建起了碧霞元君祠,此也乃一大历史奇案!清成瓘撰《伏夫子墓考》说:“冢上有碧霞元君祠,寄驾之名取此,盖谓元君驾于此冢上云尔。”此即所谓的泰山行宫。前文提到,传闻伏生墓是因碧霞元君曾寄驾于冢上而得名寄驾冢,故而在冢上建泰山行宫。又说因唐王征东寄驾于此而得名寄驾冢,无论哪种说法,皆属荒谬之论。自元之后,战乱频仍,官府对崇文尊圣之事无暇顾及,伏生后人衰落凋零,时有奸人谋划侵吞和利用伏生墓田以取利,故而编造神话传言,建道观于圣墓之上。并且直接导致圣人之墓穴易名为“寄驾冢”或“泰山行宫”。呜呼!难怪邹平大地西北的伏生墓被淡忘,难怪人们只知邹平的伏生祠、衣冠冢与齐东的寄驾冢、泰山行宫,而不知齐东的伏生墓!《齐东县乡土志·耆旧录》载:“旧城西南寄驾冢即汉儒伏生墓,后人误建泰山行宫于上,先生恻然谓无以妥灵。爽具禀当道,将行宫移建他所,而墓之周围葺以墙垣,禁樵採更,于墓侧建造飨堂,春秋奉祀并设义塾于中。”共北屋三间、大门一间,祠旁房屋六间。这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由齐东县知县宫耀月协同邑绅刘恩瀛、孙玉籣合意,将伏生墓上泰山行宫移于墓侧修建成伏生祠。民国九年时任齐东县知事的蓝鸿翥决定重修,书有《上屈省长重修伏生祠呈文》,时任山东省省长屈映光在回复指令中予以高度赞扬,嘱托安排对伏生墓祠的“妥筹修缮保护方法”,并因此给蓝鸿翥记功一次,还亲自为伏生祠题写“灵光重耀”牌匾。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省级政府官员最后一次对伏生故里祠墓的肯定。
那魏桥镇冢子村伏生墓旁果真没有祭享祠堂么?这也与事实不合。清成瓘在《伏夫子墓考》中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出始举其里数之详。记云:…必当年祠宇…犹有存者”。又,《伏夫子墓考》中尚有“附冢有方台,广数亩,在冢东南台中时有古瓦,又如古享堂之制。征君在汉时尊为先师,故其墓制享堂制亦似仿曲阜之制而为之”之考。推敲斟酌“冢东南台中”的古瓦等,似可推论认定古时伏生墓旁还有其他建筑物,这个建筑物不是人们所说的建于墓上的碧霞元君祠,而是在墓旁筑有土台为基,台上建有祭祀享堂,是实实在在的“即墓建祠”,不然于理不合。
若是,韩店镇伏生祠以官方、社会、民间祭祀为主,魏桥镇伏生祠则以伏氏家族祭祀为主。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对先人的淡忘,以及家族的衰落,此祠堂被淹没在了碧霞元君祠的喧闹声中,岁月已久,难从考证。但“附冢有方台”必是墓的附属建筑物地基,且“广数亩”,以及在“冢东南台中时有古瓦,又如古享堂之制”等,足可以令人想象高台之上,墓旁祠堂的气派。由此可认为这里曾经是故里、祠、墓兼有,并十分壮观。
五、伏生墓文物与伏生故里
汉代伏生墓的文物应该是证明伏生故里的重要证据之一。清柳文洙《重修伏征君墓碑》碑文中曰:“咸同间重修元君祠,墓基有陷者,见其中有瓦砖器皿,皆古制,断碣残蚀,尤可辨为汉征君伏生墓等字,邑人诊验得实,鳩众修复,无资而止。”又,据传旧时伏生墓附近的人们经常在墓之附近发现一些古代瓦砖器皿等是比较常见的事。民国《齐东县志·卷六艺文志》所载《伏冢古瓶》说:“清光绪间,寄驾冢赵某于伏生墓侧取土掘得瓦质古瓶二,其状相同,高尺余,腹围径尺,两端均弇,色甚苍老,见者拟为汉代古物,现存民众教育馆。其一完全,其一两端微有残缺。”又如前文中所载成瓘所说“在冢东南台中,时有古瓦,又如古享堂之制。征君在汉时尊为先师,故其墓制享堂制亦似仿曲阜之制而为之。”文物佐证虽少,然可窥见一斑。
结束语:
伏生对中国经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历史性贡献巨大,影响日益恒久绵延。一个属汉代所建大墓,实证确凿,且有后世子孙在此繁衍生息,祭祀陪伴两千年,故里在此,不言也明。现在邹平市魏桥镇寄驾冢村西北有伏生墓地,在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西有伏圣祠,皆遗址故地俱存。两处并在,足使后人行高山仰止之怀,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愿邹平能以振兴乡村文化为契机,将伏生文化建设纳入政府规划刚要,两地结合,做好邹平乡村、文化、旅游之振兴的大文章,把这块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大蛋糕做大做强!